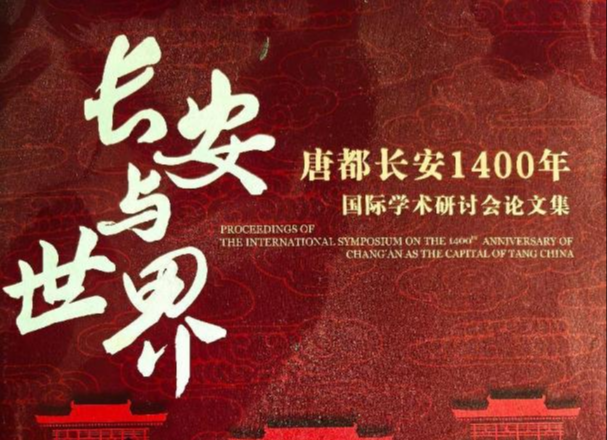读 卢 仝 笔 记
阮浩耕 原《茶博览》主编
一段辉煌的历史,其中必然有杰出的历史人物。中国茶文化在唐代的兴盛,有卓越贡献者莫过于陆羽和卢仝。诚如明人文尚宾所言:“茗饮之尚从来远矣,后世独称陆羽、卢仝。岂独其品藻之精、烹啜之宜,抑亦其清爽雅适之致,对真常虚静之旨有所契合耶。”当代茶文化研究开展20多年来,对卢仝的研究却显得比较薄弱。加强卢仝研究,是传承茶文化的需要,也是我们这一代茶人的一份责任。
近年在阅读史籍中,获得一些有关卢仝的资料,做了一些笔记,兹选录几则。
七碗茶歌的创作年代
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的创作年代,在诸多的茶诗选本中均未有注释。去年读到一篇论文,文中提到“此诗写于太和四年,即公元830年,当时卢仝正在扬州。”这似乎不当。给卢仝寄“月团三百片”的孟谏议,名梦简,字畿道,唐德州平昌(今山东商河)人。因官至谏议大夫,故卢仝诗中称“孟谏议”。据《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载,梦简,生年不详,卒于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卢仝此诗不可能作于孟谏议死后。
又据林波《钱选的“卢仝煮茶图”》,孟谏议在“唐元和六年(811)出任常州刺史。”(载《茶博览》1995年冬之卷)。卢仝此诗当作于孟谏议刺常州任内无疑。卢仝曾因避债而寓居过扬州,扬州与常州近,卢仝会有应孟谏议之邀在常州居游。从《全唐诗》所录卢仝诗作中看,卢仝与孟谏议在常州有过相聚,他的《常州孟谏议座上闻韩员外职方贬国子博士有感五首》便可证之。诗中的“韩员外”即韩愈,其时应在元和三年(809)前后,孟谏议刺常州应在此间。卢仝此诗约作于元和六年(811)至长庆
三年(823)之间。
“文字五千卷”之讨论
卢仝《茶歌》中“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二句,贵州省社科院文学所王建先生根据卢仝倾向道教来考证,认为“文字五千”就是指老子《道德经》。卢仝《杂兴》诗中有句:“三五图书旧揣摩,五千道德新规矩”。此处“五千道德,”实指五千文字的《道德经》。
王泽农先生同意王建的解读。他在为《茶博览》撰《王建〈玉川茶歌献疑〉读后》一文中说:“我从北宋诗人梅尧臣的《尝茶和公议》”诗中的“莫夸李白仙人掌,且作卢仝走笔章”诗句,和清林则徐福州贡院“攀柱天高忆八百独寒到此莫忘修士苦,煎茶地胜看五千字个中谁是谪仙才”联文,都将玉川《茶歌》与李白《玉泉仙人掌茶》并列,联文并提到“文字五千。”完全同意王建同志的观点。
对王建提出将“唯有五千卷”应改为“唯有文字五千言”,王泽农先生则认为未必。他说:“从汉语语法来看,‘唯有文字五千卷’句中的主语是‘卷’,它的状语可以是‘五千’,这二字的词组,也可以是‘文字五千’四字构成的词组,可以译成现代汉语‘文字五千构成的那一卷书’。这与王建同志的观点就一致了。”
卢仝隐居洞山
明人周高起《洞山芥茶系》有记:卢仝《茶歌》云:“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又云:“安知百万亿苍生,命坠颠崖受辛苦。”可见贡茶之苦,民亦自古然矣。至芥茶之尚于高流,虽近数十年中事,而厥产伊始,则自卢仝隐居洞山,种于阴岭,遂有茗岭之目。相传古有汉王者,栖迟茗岭之阳,课童艺茶,踵卢仝幽致。
卢仝曾在常州和扬州寓居过一点时间,这在他的诗作中都有过记述。除了前面已说明的两首外,还有《扬州送伯龄过江》,明确卢仝时在扬州。另有《亿金鹅山沈山人二首》和《赠金鹅山人沈师鲁》,其中有句:“金鹅山中客,来到扬州市。”可见卢仝此时亦在扬州。周高起所说:“卢仝隐居洞山,”虽然目前尚是孤证,但从卢仝的诗作和在扬州、常州的行止考察,此说还是可信的。
关于卢仝的卒年
马舒先生有《志怀霜雪,操似松柏——卢仝的为人及其不是死于“甘露之变”说》一文,刊发在《茶博览》2001年第2期。文章认为卢仝并非死于唐文宗太和九年(835)的“甘露之变”,其根据,作者在文末声明:“本文主要论点,参考中华书局《唐才子传校笺》(二)卢仝篇。”
马舒先生此文寄我时,曾附上《唐才子传校笺》卷五“卢仝篇”的复印件。读后感觉马先生文与“校笺”所述内容与观点一致,亦为卢仝研究中的学术探讨,所以刊发。
近日,找来《唐才子传校笺》重印本看。发现重印本共五册,前四册是对《唐才子传》十卷的校笺,分别于1987-1990年间出版。其中第二册卷五卢仝篇,有苏州大学吴企明先生笺证。1995年又出第五册,此册是对前四册校笺的疏误所作的补正。其中“卢仝篇”有陈尚君先生补正。补正原笺卢仝死于“甘露之祸”“其事实不可信”的断言。对原笺的三条举证:1、“唐史无此证载,”诸史言甘露事变“均未提及卢仝;”2、年岁不合;3、仝子添丁,生于元和五年,贾岛有“托孤”之语,若卢仝死于甘露事变,则添丁已长大成人,何来“托孤”。
由此可见,马舒先生在为《茶博览》撰文时,没有看到或么哦有读到《校笺》第五册。
曼生刻卢仝诗句于石
与陈文述、陈甫并称“武林三陈”的陈鸿寿,博学工诗,还以他创制的曼生壶名闻后世。曼生仰慕卢仝,并爱其茶歌,自刻“纱帽笼头自煎吃”小印一枚,又作长跋云:
茶饮之风盛于唐,而玉川子嗜茶,又在鸿渐之前。其诗有云:“柴门
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使后之人,味其词意,犹可想见其七碗吃余,两腋风生之趣。余性嗜茶,虽无七碗之量,而朝夕所啜,惟茶为多。自来荆溪,爱阳羡之泥细腻可以为茶器,故创意造型,范为茶具。当午睡初回,北窗隅坐,汲泉支鼎,取新茗煮之,便觉舌本香清,心田味沁,自谓此乐不减陶公之羲皇上人也,顾唐宋以来之茶,尚碾尚捣,或制为团,或造为饼,殊失茶之真味。自明初取茗芽之精者采而饮之,遂开千古茗饮之事,使卢仝生此时,其称羡又不知当如何也。余故刻卢公诗句于石,而并为跋,亦以增艺技一韵事也。
卢公饮茶之风如此为后人所仰慕,卢仝茶歌千年来如此为后人吟咏不绝,如卢公地下有知,真不知道如何也!
《煎茶七类》与卢仝
《煎茶七类》一篇辑入陆树声《茶寮记》。在浙江上虞天香楼主人王望霖所藏历代名家墨迹中,有绍兴青藤道士徐渭的“煎茶七类”行书真迹。两者内容大体相同,文字上有多处增删。今人关注的倒不在文字增删,而在徐渭书作后部的跋文:是七类乃卢仝作也,中秋甚疾,余临书稍改定之。时壬辰秋仲。青藤道士徐渭书于石帆山下朱氏之宜园。
以上徐渭所言,且又系手书真迹,是有相当可信度的。便在稍改定后予以书录。
《煎茶七类》究竟是陆树声作,还是卢仝所作,尚待考证。
“七碗”并非有形之饮
对卢仝的“七碗茶,”有人解释的很实:“由于茶叶好,所以一连吃了七碗,作者细细品味,每饮一碗,便有一种新的感受。饮到七碗时,更觉得两腋清风,飘飘欲仙了。”“诗人写煎茶、饮茶,一口气饮了七碗,饮每碗都有不同的感受,最后饮到飘飘欲仙,想乘风归去。”如此解读,太过于拘泥。
明人喻政《茶集》附有:“煮茶图集,”辑录了多位文士观赏唐伯虎
画陆羽煮茶图的题跋,其中有于玉德的一则,说到了七碗茶:夫饮酒者,一饮一石,此不知酒也。饮茶者饮至七碗,则亦不得。夫有形之饮,不过满腹传玩之味。淡而幽,永而适,忘焉,仙也;怡焉,清也。
饮茶分“有形”与“无形”。“柴门反关无俗人,纱帽笼头自煎吃,”是有形之茶。“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是无形之茶。
玉川之志,独昌黎知之
刘松年绘有《卢仝煮茶图》,清人胡敬有一则题跋:
右玉川子煮茶图,乃宋刘松年作。玉川子豪宕放逸,傲睨一世,甘心数间之破屋,而独变怪鬼神于诗。观其茶歌一章,其平生宿抱忧世超物之志,洞然于几语间,读之者可想见其人矣。松年绘为图,其亦景行高风,而将以自企也。玉川子之(志)向,洛阳人不知也,独昌黎知之。去昌黎数百年,知之者复寡矣。
韩愈与卢仝的相交相知,《唐才子传》有记:“时韩愈为河南令,爱其操,敬待之。尝为恶少所恐,诉于愈,方为申理,仝复虑盗憎主人,愿罢之,愈益服其度量”。此时间应在元和五年之六年,即810-811年。
韩愈对卢仝的《月蚀诗》非常赏识,以致他校卢仝作《月蚀诗》一篇,大半用玉川子句。
以上数则,仅是阅读笔记,积累资料,存点滴所思,备作研究。今摘录出来,为与同好者互相交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