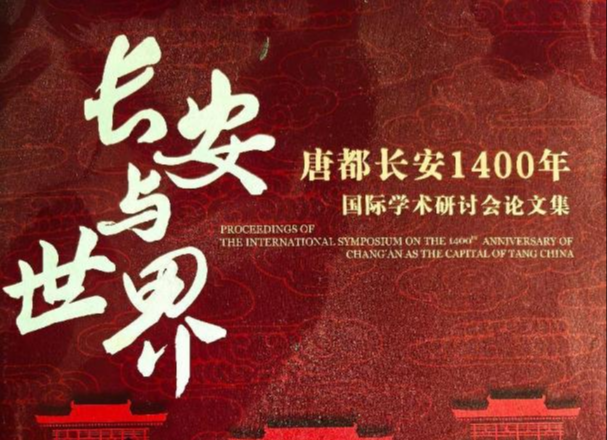论卢仝的儒学思想
鞠 曦
卢仝是生活于中唐时期的儒生。据本书《卢仝评传》的考证:“卢仝出生于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5年),死于唐文宗太和九年(公元835年)的‘甘露之变’”。由于唐代文化思想“不入于老,则入于佛”(韩愈:《原道》),所以唐代的儒生,在老佛为主流的思想环境中,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生活方式上,无不显其二难困境。因此韩愈力排佛老而发道统意识,为复兴佛学作出了努力,为宋儒的道统谱系作了理论上的铺陈。我们看到,正是在唐代这种文化思想环境中,出现了本书的主人公——被后世称为茶仙的玉川子卢仝这样一个人物。历史表明,卢仝其言其行为中国文化留下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为中国文明增添了色彩。
现存的文献资料表明,卢仝传世的主要作品是为数不多的诗词,其虽著有《春秋摘微》,却因故而未能传世。其最著名的作品是《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的数句茶诗:“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载《全唐诗》卷三百八十八,《卢仝二》)。这数句茶诗,被后人称为“七碗茶歌”。在盛行“茶道”之后,“七碗茶歌”随之走向了世界。“七碗茶歌”的文化底蕴,重在表达了儒生在失落的文化氛围中的所思所想,其在形似喝茶实为悟道中充分表现了中国文化的儒生情结。显然,七碗茶歌无论在文化意义上还是在思想意义上,尤其在“茶道”的文化普适性上,以其儒生的忧患意识,不断唤起人们的理性思考。这是卢仝为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所以,由于上述原因,在盛行茶道的国家,卢仝成为一名知名的人物,这是一种必然。然而,尽管这样,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有关卢仝的研究却远远不足,在许多方面存在空白。应当说,此前所作的卢仝研究,仅限于以“七碗茶歌”去了解卢仝。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了李菊月先生的《卢仝评传》问世。观其内容可知,该书是为填补卢仝研究的空白之作。在作者数年的辛勤劳动下,在资料十分奇缺的条件下,考证而旁通,择引而力证,拨开了笼罩在卢仝身上的迷雾,从而为深入研究卢仝拓展了新的方向。
由《卢仝评传》而有所发,我认为应在这一研究基础之上,进行卢仝思想研究。历史表明,既然卢仝因“七碗茶歌而成名于茶道文化、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之中,就更应由此研究卢仝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中的意义。尽管他没有留下足以传世的思想作品,甚至不能以儒家而称谓之,但正因为如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因“茶道“和诗词而成名的一个人物,对知识分子而言,尤其自认家门而称道为儒者之人,卢仝的思想就更有广泛的代表性,从而使卢仝和他的思想具有不可忽略的地位,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史、道学与儒学思想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史资料。
之所以要把卢仝研究提高到思想史的高度,是因为卢仝的人生理想,自出隐于王屋山而归于儒门之后,其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卢仝才华横溢,一生布衣,负有经世之奇才,却无用武之寸地。卢仝早年好道学,几经生活磨难,受韩愈的影响而服膺儒学,中年亡于“甘露之变”而未得善终。虽然生奉无道之世促成了卢仝之悲剧,但就其思想的具体价值而言,不能不认为其实是由汉唐儒学的思想误区所导致。
儒学思想史表明,自孔子之后,儒学曾有两辟一建。所谓两辟是由孟子辟杨墨和韩愈辟佛老,所谓一建是由朱熹等宋儒建立的中国文化道统谱系。孟子辟杨墨是因为“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韩愈辟佛老是因为“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子,不入于老,则入于佛”(韩愈:《原道》)。中国文化,自“道术为天下裂”(庄子《天下》)之后,孔、老生逢二千五百年之时,为使道济天下,老子学以载道,撰以《老子》。而孔子则对此前二千五百年的“郁郁乎文哉”(《 论语·八佾》)“巍巍乎其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整理编纂。为使文以载道,孔子纂成《诗》、《书》、《礼》、《易》、《乐》、《春秋》六部经典,以此厘定了中国文化之道,即所谓“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史记·太史公自序》)。然而,由于暴秦之火,在两汉统校经书之后,由汉儒“独尊儒术”的价值取向所决定,失落了孔子一以贯之的中国文化之道。所以才有所谓两汉以后的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阳明新学、现代新儒学的思想重构,然而,却终究未能与孔子厘定的中国文化之道一以贯之。
韩愈生逢唐代,在儒学失落的情势下,面对“不入于老,则入于佛”的文化态势,其把辟佛老而振儒学作为自己的任务。他把辟佛老而振儒学作为自己的任务。辟佛尚有学理的依据,然而,其辟老。则是源于秦汉以来“儒道相绌”之误。关于“儒道相绌”,史马迁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其谓是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由此可知,“儒道相绌”之误,始于对孔子之道的误解。由于“儒道相绌”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中的误区,所以,韩愈也就必然成为误区中的儒家。韩愈认为:“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韩愈《原道》)韩愈视老子为“坐井而观天”的井中之蛙,而孔子却说“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孔子家语言·观周》),由此可知韩愈所失孔子之道而误于“佛道相绌”也。韩愈所道者:“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韩愈《原道》)。显然,韩愈之“吾所谓道也”,意在承尧舜禹汤周公孔孟。所以这种气度和学理足以使韩愈成为一代名儒而使卢仝折服,卢仝出王屋山而归儒林,也就成为必然。然而,韩愈的儒学之误,不但误己而且误人,由此引发出卢仝的悲剧色彩也就必不可免。
韩愈辟佛老,为儒学在唐代争得了一席之地,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孔子儒学道在“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周易·说卦传》),并重在以是践履。由于韩愈不知,自然无法实行。儒学思想史表面,韩愈虽然辟佛老而发道统意识,但在朱熹等宋儒建立的道统谱系中,却没有韩愈的地位,这也在另一个方面表面了韩愈的儒学之误。
韩愈辟佛老而振儒学,使他成为一代名儒。所以受“唯有河南韩县令,时时醉饱过贫家”(《苦雪寄退之》,载《全唐诗》,卷三百八十九,《卢仝三》)的韩愈所关心的卢仝,受其影响而服膺儒学,也就在情理之中。从韩愈对卢仝的评价:“先生事业不可量,唯用法律自绳己。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穷终始。……先生抱才终大用,宰相未许终不仕。假如不在陈力列,立言垂范亦足恃”(《韩昌黎文集》第169—170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4月第一版)中更显其二者志同而道合。因此,卢仝早年向往道学而自乐于王屋山,中年受韩愈的影响而以儒自命,亡于“甘露之变”而终其一生,其悲惨的结局,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不能不认为是宝贵的历史资料。卢仝因受韩愈的影响而成为悲剧式 的人物,进而对韩愈的思想理路进行反思,这对于道学和儒学思想的计较研究,孔子之学和老子之学的比较研究,以及汉以后儒学思想史研究,尤其对于中国文化思想理路的正本清源,具有重要意义。
悲剧式的人物,都具有二难困境,所以,卢仝也不能例外。卢仝服膺儒学之后,在生不得志、漂泊不定的生活中,一旦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受挫,就“初岁学钓鱼,自谓鱼易得。三十持钓竿,一鱼钓不得。人钩曲,我钩直,哀哉我钩又无食。文王已没不复生,直钩之道何时行”(《直钩吟》,载《全唐诗》卷三百八十二,《卢仝二》)而嗟叹道之不行,进而对儒学产生怀疑:“昨日之日不可追,今日之日须臾期。如此如此复如此,壮心死尽生鬓丝。秋风落叶客肠断,不办斗酒开愁眉。贤名圣行甚辛苦,周公孔子徒自欺。”(《叹昨日三首》,载《全唐诗》卷三百八十八,《卢仝二》)久经世道险恶之后,随着卢仝儒学理想的破灭,其甚至想重归山林,不问世事:“蛇毒毒有形,药毒毒有名。人毒毒在心,对面如弟兄。美言不可听,深于千丈坑。不如掩关坐,幽鸟时一声。”(《掩关铭》,载《全唐诗》卷三百八十九,《卢仝三》)从卢仝写有《春秋摘微》而论,如果不是在刚届不惑之年而死于非命,他的思想可能走向成熟。或者如韩愈所言,卢仝能写出“立言垂范”的不朽之作。卢仝早年好道,居王屋山却不得道旨,服膺儒学而不得其位。受韩愈影响,其不但不理解老子之道,也不理解孔子之学,“周公孔子徒自欺”,最终对周孔之道产生了怀疑。所以有理由认为,卢仝的儒学思想,是在汉唐后儒的误区之中,最终而非道非儒,落得死于非命。
孔子曰:“笃信好学,死守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秦伯》)卢仝适逢唐元和、长庆、宝历年间的宦官当权而天下无道,“贤名圣行甚辛苦”,服膺儒学而死于“甘露之变”,说明他并不理解孔子的儒学之道。其作《春秋摘微》则表明,卢仝同样是以汉儒的理路,以《春秋》推定孔子的儒学思想,然而,这却是后儒的误中之误。关于汉儒之误,我在《中国之科学精神》(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第183—18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中论证了一点,在此不赘。所以,韩愈和卢仝对老学之误,不但因于“儒道相绌”且因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儒学之道在孔子之后的失落。尽管卢仝早年居于道教的第一洞天王屋山,由于不解道学之本,使之在思想道路上和韩愈同样有辟道学之举。他在《忆金鹅山沈山人二首》中说:“莫合九转大还丹,莫读三十六部大洞经。闲来共我说真意,齿下领取真长生。不须服药求神仙,神仙意智或偶然。……呜呼沈君大药成,兼须巧会鬼物情,无求长生丧厥生”(《忆金鹅山沈山人二首》,载《全唐诗》卷三百八十八,《卢仝三》),其嘲笑道学之意,由此可见一斑。
由两难困境所决定,卢仝顺境之时,则“天生圣明君,必资忠贤臣。舜禹竭股肱,共佐尧为君。四载成地理,七政齐天文”(《感古四首》,载《全唐诗》卷三百八十八,《卢仝二》);“意智未成百不解,见人富贵亦心爱。等闲对酒呼三达,屠羊杀牛皆自在”(《杂兴》,载《全唐诗》卷三百八十八,《卢仝二》)。其逆境之时,则“秋风落叶客肠断,不办斗酒开愁眉。 贤名圣行甚辛苦,周公孔子徒自欺”,(《叹昨日三首》,载《全唐诗》卷三百八十八,《卢仝二》)“不如掩关坐,幽鸟时一声”,以此表明了卢仝二律悖反的心态,究其实,是难能“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也。
由于失落了孔子“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哲学性和科学性的思想体系,儒学步入了思想误区。孔子之后,历代儒家几乎都把“仁义之术”推定为孔子的核心思想,如韩愈所论“夫所谓先王之教也,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韩愈《原道》),由此谓儒学之道。韩愈虽指出有《易》之为文,但他认为《易》同样为“仁义之术”。而后儒的问题正是表现在对《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误读。当然,对《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误读,不是始于韩愈,其在孔子之后就开始了,以至于孔子有“后世之世疑丘者,或以《易》乎”(《帛书要》)的正确遇见。
问题表明,中国思想史的正本清源,尤其是儒学思想史的正本清源,是现代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在正本清源之前,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及其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等问题,则无从谈起。谓以“中体”及“复兴”者,是谓道学乎?儒学乎?或是两汉经学、魏晋玄学?甚或宋明儒学、阳明心学及现代新儒学?!问题表明,正本清源之前,以“体”言及复兴中国文化者,空言妄论也。儒学思想的历史和逻辑理路所证明的是,儒学在汉代以后,由于失落了“一以贯之”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孔子之道,因此才发生了儒学的历史与现代危机。而卢仝其人,正是儒学在历史危机中的牺牲者,因此,其悲剧一生,与口诵新惟的“七碗茶歌”形成了鲜明的反照。
所以应注重研究卢仝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中的意义。在济源召开的“第二届古天文与中华传统文化暨王屋山古文化国际研讨会”期间,我把这个意见向李菊月先生表明之后,她邀我为之作序,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毫无疑问,《卢仝评传》所作的工作是值得称道的。如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把卢仝放到这个文化思想史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就会从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史的高度发现卢仝其人其行所代表的儒生的二律悖反心态及其对两汉以后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当然,这是一个较大的研究课题,或许只有生存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中国现代学人,才可能在进一步解读卢仝其人的基础上,完成这一工作。
因此,我希望李菊月先生在本书的基础上,再写一本《卢仝思想研究》,以唐代的儒学思想为主线,深入挖掘卢仝和韩愈的思想关系,烦死卢仝思想的时代性,厘定后儒的思想误区,从而把卢仝的个案研究,与中国文化思想的历史与逻辑统一。这一工作,不但对于中国思想史研究具有折腰价值,而且对于复兴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将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
以是为序。
2001年10月于长白山恒道斋